大家好,今天小編關注到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話題,就是關于我變了沒變鋼琴版音樂的問題,于是小編就整理了2個相關介紹我變了沒變鋼琴版音樂的解答,讓我們一起看看吧。
相信很多人都有吧,會有那么一首歌讓你一直單曲循環聽!聽的是旋律,聽它的詞、曲。讓你百聽不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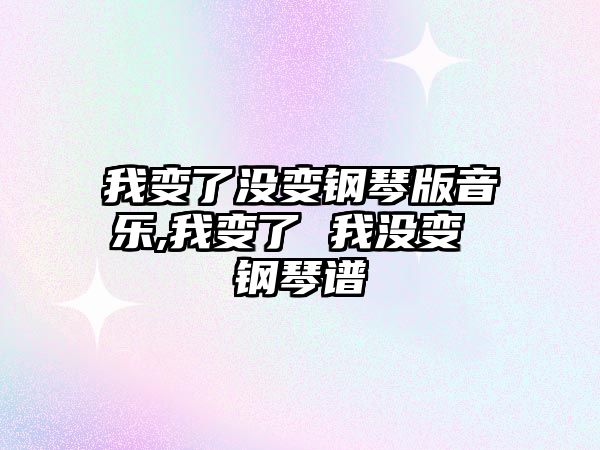
《光明》
很喜歡的一首歌,每一次聽到這首歌時,相信光明的道路就在前方!!
謝敬!
有這么一首歌,讓我在入睡晚安之前不斷循環播放!是因為有了這首纏綿悱惻的歌聲與詞曲 ,縈繞與心際之間!才下眉頭,卻又上心頭!這就是一首,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!
因為最近陷入了深深的感情里,不能自拔!所以就讓這首歌來麻醉自己!讓我在病痛快樂著!享受音樂給我帶來的迷醉!在不知不覺中!就沉睡過去了,等一覺醒來!歌聲還在多情的唱著!這才恍然大悟!該是天亮了!明天還要繼續!!
那好!我就把這首歌寫給網友們吧!
你問我愛你有多深,我愛你有幾分,你的情亦真,你的愛亦真,月亮代表我的心,輕輕的一個吻,已經打動我的心,深深的一動情,叫我思念到如今!……
帶著美好的遐想,很快就進入了夢鄉!夢里相見美好如初!這是一件多么愜意的事呢?!捎去遠方的思念!!暫慰了卻無痕!!!(杜撰而已!為了文章好看)!此地無銀三百兩!請友們猜猜!!!
(謝悟空!謝閱)!
(2、20)完稿!
我昨天晚上聽周深演唱的《有可能的晚上》,覺得好動人啊。
輕輕的念白,那淺淺深深的歌詞,緩緩的訴說……
不是那種激烈的感覺,是那種淺淺美好的感覺,是生活的感覺誒。
我當時想到了漢樂府里面的美女羅敷,當然也想到了西方特洛伊戰爭中的美女海倫。
一個美得讓人覺得歲月靜好。
一個美得讓人競相爭執戰爭。
大概是東西方,對于美好定義的不同。
或者,更多的是每個人對于美好的定義不同吧。
我一向覺得,文化和教育,才是將人真正區分的地方。
并不是東方西方這種地域吧。
或者每個人,每個時間段都可能是不同的。
接受自己的不同,接受自己的不一樣。
然后明白那句:我要快樂,不必正常。
我不知道周深唱的時候,想起了誰,才會如此訴說。
我只知道,聽歌的時候的自己,竟然會想起一些歲月了。
片段,零落,點點星星。
同樣的一首歌,我又聽一下原唱,曾軼可的版本。
就多了許多的俏皮。像一個小女孩在愛里面的欣喜與嬌嗔吧。
明明旋律是一樣的啊,歌詞是一樣的啊。
但是,不同的人演繹的,的確都是不同人的版本。
聽歌的人其實也是如此吧。
明明是同一首歌曲,每個人聽到的,可能都是自己的故事了。
聽到的,可能都是自己的情緒了。
我想起了我會喜歡的詩歌。
我自己讀過許多次的詩歌。但是,有沒有一次是一樣的呢?
好像面對特別多的人的時候,大概是一樣的。
我記得,以前,在線下講課的時候,面對很多人會朗誦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開”。
那個時候,我好像是想要堅定自己的一點點希望和信念,關于生活,關于生命的。
可是,到后來呢?
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,每一次讀到詩歌,哪怕是同一首詩歌,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。
我每次想到不同的人的時候,訴說的那種感覺也是不同的。
原來啊,每一首詩,其實都是有一個對象的,唯一的目標對象的。
就是講給她聽,講給他聽,或者就是訴說,淺吟低唱。
詩歌應該不是用來朗誦的吧?
可能,與我來說是用來訴說和講述的吧……
可能就是,我有許多話要說于你聽,不知從和說起,不如,我先講個故事給你……
那里面,可能會聽出熟悉。
《尋》《巨鹿》和這兩首歌的純音樂伴奏很適合睡前聽
《枕邊故事》也是很溫馨的一首歌,睡前聽感覺就像聽一首很溫暖的童謠~
還有我喜歡的純音樂《琵琶語》《風吹過的街道》和久石讓的一些曲子都很不錯
我住在北京。北京的西三旗,有一個農貿市場。一次,我看到了一個老太太,去買刀魚。
市場里的商戶們,好多人都認識她,主動和她打招呼。
老太太來到了一個攤位前問:“您好,您這刀魚多少錢一斤”?攤主回答:“這是深海刀魚,天然的,五十元一斤”。“您吶,給我拿幾條”。攤主拿了兩條,老太太說,再拿。攤主拿了五條,老太太說,再拿,再拿!攤主拿了十條。
十條,一上稱,十六斤,攤主算賬很快,八百元。老太太拿出了八張百元大鈔遞了過去。老太太也會用“微信”,但老太太偏愛現金,不屑使用微信付賬。攤主沒敢驗鈔票的真假,也沒有去數,就直接把錢收到箱子里去了。
攤主客氣地問老太太:“我把魚給您收拾好了”?老太太說:“不,不,您收拾得不干凈,我回去自己收拾。你把魚頭和魚尾給我剁下去,就行了”。
攤主把十條魚的魚頭和魚尾剁了下去。老太太抬頭一看;說不行,不行,用手比劃著,再剁,再剁!攤主只好重新把魚剁了一遍。這會兒,挨著魚頭的,有肚腸子的那一段;挨著魚尾巴的,比較細的那一段,又被剁下去了。
攤主說,給您魚。老太太說,這兩頭,還得剁,還得剁!攤主無奈。又狠心剁了一遍。一條刀魚能有多長?怎么能架得住這樣剁?這回,只剩下中間的那一小段了。
老太太滿意了,發話了,您給我裝上吧。攤主走出攤位,把剩下的刀魚遞到了老太太手上。也就剩四,五斤吧。
老太太滿意了,滿足地走了。攤主還在后面叫:“老格格您吶,慢走,剩下的魚怎么辦”?老格格回答:“喂貓吧”!
原來,老太太是一個“老格格”。不過,我想了一下,感覺歲數有點不對。雖說北京遺留的老格格不少,可這老格格還是有點太年輕,應該是老格格的女兒,“小格格”吧?
這就是,“小格格三剁刀魚”的故事。不,不!這不是“故”事,這是“真”事。是我親眼所見。(配照為我的親拍作品,“小格格”)。
到此,以上就是小編對于我變了沒變鋼琴版音樂的問題就介紹到這了,希望介紹關于我變了沒變鋼琴版音樂的2點解答對大家有用。